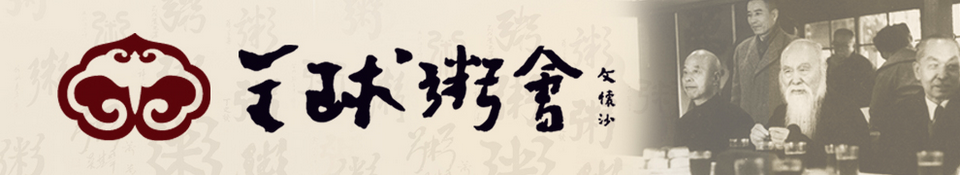和尚打籃球被視為佛門異類 事母至孝奉養天年傳為佳話





理由在於大師宿願得償,2009年佛光山成立「三好體育協會」,以「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為主旨,來推廣全民體育活動,經由各項運動競技,來接引青年學佛,指日可待;然而,陸炳文想的更多、更遠,因為星雲還是小和尚時,打籃球曾被當成異類,而被佛學院勒令退學,差點遭逐出佛門的憾事,從獲勝掌聲中已視為平反。
有一回聚會,意欲傳承光大宗門,在臨濟宗佛光山傳燈樓,大師給佛光弟子、在家居士傳法、講授日課,我聆聽言及過往「在佛教學院念書,就提倡打籃球,但打籃球給老師看到,是會被開除的,卻寧可被開除,還是喜歡打籃球。後來到了台灣,教書之餘,就是提倡打球,但是台灣的學生不敢打籃球,甚至我拿球給他,他就往後退,讓我覺得很遺憾:過去做學生,老師不准打球;現在做老師,學生不敢打球」。
再拜讀大師鴻文〈在球藝中學做人〉,印證先前所言不虛,進而直覺當前學子有多麼幸福,佛光子弟尤其有多幸運,有書讀、有球打,甚至未來出路皆有保障。那是星雲面對普門中學女子籃球隊職員,時間2004年3月16日,地點也就在傳燈樓梯形會議室,大師開示:「我們的人生要多采多姿地活下去,就像我們的生命,要靠讀書、修養、道德或是宗教情操來豐富;我們的興趣、健康,則要靠運動來鍛鍊。
「我是非常熱愛籃球運動的,⋯⋯。30幾年前,我在佛光山發展,乃至在全世界各地建寺廟,均因建了一個小小的籃球場,和100多個學生一起打球,而覺得特別歡喜⋯⋯。我們普中女子籃球隊,有什麼優厚的條件?打球是年輕的時候打,人的生命是一生一世的,球員在球場上為團體爭光,為國家爭光,到了力量用完,打球年齡過去,就沒有人聞問,這會讓體育界的優秀人才感到灰心,他們皆看不到未來。
「佛光山的女子籃球隊不一樣,我們是一個有理想、有未來的球隊。比方練球,希望每年至少有一、二次到韓國,或是美國、日本去打球,與不同國家的人以球會友。所以我們不只是台灣的球隊,我們未來是一支國際性的球隊。⋯⋯假如我們的女子籃球隊,將來成功,可以跟國際佛光會合作,把我們球隊帶到全世界去,樂於以球廣結善緣」。
以上賽事球場所見,面會星雲當場所思,鴻文內容當中所讀,陸炳文從中一再領略到,在球藝中學做人的道理之外,乃至體會出今後的希望,包括:大至籃球運動蓬勃大發展前景,中為普門中學、佛光大學籃球隊戰績大前程,小到小球員們事業遠大前途,如同大師篤定保證,「只要你們有條件,絕對不會辜負你,一定給你成長」。誠哉斯言。
16、事母至孝奉養天年傳為佳話





那一天日子好,我南下佛光山,拜見星雲大師,呈上祝壽禮物,《陸炳文的兩篇論文》乙書,其中一篇〈許慎與丁福保/請問貴姓〉(2006年岀版)大師特别感興趣,還即時當著老友、許慎編著說文解字學專家、許家璐的面翻閱,自稱對上海粥會1924年始創人,寫過《丁福保傳》當作第三類教科書,傳記指岀:丁福保由於其兄與吳稚暉、陳仲英相友善,故亦常追隨諸先生後,飽聞吳先生等,縱論學問文章,得益良多。
那天我才察覺到,星雲早歲的自學、自修也能飽讀詩書,對照《迷悟之間7》:〈生活的情趣〉大作,再度提到粥會精神導師吳稚暉,強調守道守德的堅持,也不能說不重要時,特別舉岀今古,3個堅持事例:近代的吳稚暉堅持,不在政府裡,求得一官半職;媲美古代陶淵明堅持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另有嚴子陵堅持的,不做漢光武之臣子。
孝順大師小結:凡是好的,我們希望世界人類都能堅持;凡是不好的,我們希望大家也都能放棄。忠臣孝子,也都是靠著自己的堅持,才能成為忠臣孝子。陸炳文受教了,大膽接話回應:當年臺北粥友,支助翻新吳稚老在江蘇常州武進的、雪堰橋故居內部裝修階段,我們堅持把象徵至孝篤親事母、卻無法頤養天年之跪母石,保留下來不得放手拋棄,恰是奉行此意,雖說舊石破皮,照樣視同寶石,妥善存藏留念。
星雲作《迷悟之間》:〈造字〉篇文曰:中國造字很有趣味,例如有人問吳稚暉:「為什麼叫"波"?」他回答:「水的皮」。又問:「為何叫 "坡"?」他說:「土的皮」。由此而推,什麼叫"被",就是衣的皮,用布衣做皮,就是"被";人為什麼會"疲"倦?因為生病,從皮膚的顏色就可看出端倪。我以此類推:什麼稱之"破"?石頭的破皮,故外貌不揚,跪母石固皮相不佳,可是內蘊飽含深意,精神價值超乎想像!
過去人們常講,誰很皮,很不乖,皮小孩,調皮搗蛋,然而長期觀察下來,這種人並非不孝順,長大也不會不長進;所謂孝者不外乎順,聽他人良心的話也。我總以為,星雲正是這樣的皮,只在表相,表面上看,活潑外向,但大師不只想到自己,相對於此(本人),還有她(他)、別人的存在,用一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從彳字部首、亦即雙人旁皮字"彼",「對此稱彼也」《玉篇》,「知彼知己」《孫子.謀攻》。
星雲談母親:「她要我們目中有人,心中懷有眾生」。這就在講"彼"字,《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稱,母親一生中有件最得意事情:1990年,來到她兒子創建的台灣佛光山,在兩萬人的信徒大會上說:「過去觀音菩薩,在大香山得道;我則希望大家,在佛光山得道。愧彼贈我厚,我沒有東西給你們,只有以此饋彼,把我的兒子送給大家」。
大師曾在洛杉磯西來寺的佛殿宣講,陸炳文一旁洗耳恭聽佛法:「有一次也是在西來寺,我講《金剛經》,不知道母親就坐在後面聽,等我下來了,她批評我,講得太高深了,怎麼可以告訴大家『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
「『無我相』倒也罷了,如果『無人相』,心中眼中都沒有他人,没有"彼"在,還修什麼行呢? 同時領悟到,母親堅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間佛教的註解。母親隨時為我們說法,可以說她是一部人我關係學:《"彼"學》、或《人學》的經典,她要我們目中有人,心中懷有眾生」。
當時我仰望堂上1999年,李自健繪製的油畫〈慈〉作,畫中主角即星雲母親、李劉玉英老奶奶也,直觀講師是母親的聽眾,我乃孝順大師忠實讀者,讀其書如讀其人"彼",可曾讀懂又讀通"彼"。今在臺北自宅回眸,童年與母親的合影,反躬自省捫心自問,此生有孝而順"彼"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