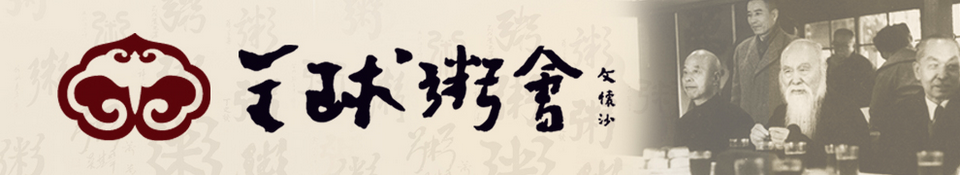平常老人的平常兒子(6之4)* 狄源明
更新时间:2012-11-14 来源: 发布:狄源明 浏览:
党與非党人士聯合政府的誕生,證實人民政府在兌現民主原則。可惜好景不長,不到7年,又演變為一黨專政了。新政權在收繳槍支、登記散兵游勇舊政權人員、禁毒、槍斃天津兩個貪污的專員級的官員,嚴懲囤積麵粉的奸商、封閉妓院(妓女在教養院中控訴老闆、鴇母、打手,治癒性病後,可自選對象嫁人;或參加培訓當紡織、針織工人或防疫隊員,電影《姐姐妹妹站起來》述自食其力教育等甚詳),偷盜、搶劫事件大減,“同志”這個平等的稱呼代替了先生、老爺、小姐等,“車夫”也改稱“三輪車工人”。
有一次,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舊“太廟”)看籃球比賽,見朱德總司令穿件白襯衫與普通觀眾坐在一起,只是身邊有個警衛員。一股工農解放、男女平等、服務光榮、改造陋習的清新之風使社會生機煥發。誰要是訓斥群眾、強迫命令、拖宕工作,就是沿襲“國民黨作風”,會被同志嚴厲批評。
寄託著四川百姓四十年願望的成渝鐵路兩年多便建成通車了。大家對國家前途滿懷信心和熱情。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均慷慨解囊,我們敢同美帝較勁,多麼揚眉吐氣。街頭活報劇中美國總統氣急敗壞的小丑形象,總是笑駡的活靶子。
1951年冬,我參加中央土地改革團華東第六團到安徽阜南縣搞了兩期土改共三個多月。讓農民明白“誰養活誰”和如何劃分階級,把地主的五大財產(土地、房屋、牲畜、大農具和浮財)分給貧、雇農和下中農,也給地主按人口留一份。富農的多餘生產資料也要徵收。土改結束離村,男女老少敲鑼打鼓放鞭炮,排成長龍送我們走出幾里地,的確是由衷的熱烈。
“我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委員,逃往臺灣了”——這塊大石壓在我背上,是我的原罪。“清理中層”忠誠老實運動,三反運動後期向党交心、重點“解剖”……我一次次在黨內外的會上批判父親對我的思想影響,向朱德學習——背叛所出身的家庭,向無產階級徹底投降。我說:我父親叫我在亂世中“搶讀”,希望我成名成家;還督我學四書、讓我們辦《家風》報,不斷灌輸封建思想;我吃剝削飯長大,思想感情與工農兵有大差距……
1953年春,讓曾學理工農醫的大學生學有所用,我被安排到市衛生局的衛生防疫部門,貫徹“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等方針。
1954年初,我與21歲的北京李姑娘締婚,她高小畢業,任區政府文書屢受獎勵,在業餘中學也是模範學生,是個處處要強、感謝共產黨給予學習培養和工作機遇的新黨員。我倆在許多方面互學互補,她處人比我平易、謹慎,更能替別人著想。後来,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很優秀,一個是英語高級教師,另一當過外貿公司的副總經理。
第二樂章 沉重 (1955~1978)
1955.7由反胡風開始的“肅反”運動把我“揪”出來大審大批了半年,主要是父親和其他“反動親屬”與我的關係,需滴水不漏地向圍攻我的幾十位群眾從頭敍述,一一回答他們的質疑,然後寫成文字,再問、再答、再寫……外調同志根據線索四處尋詢證人,讓他們詳寫旁證材料。
有個市衛生防疫站同志,過去曾與我私下談心,在會上似乎頗有奇貨可居,大揭我談的家庭狀況、上學經歷以及對防疫站長、同事的一些看法(倒是沒怎麼添油加醋),好在我確沒有對中共和領導人不敬,也沒把柄落在他手。
在這半年中,停止了我的業務工作,讓我獨自呆在辦公室裏(作為市衛生防疫站的衛生科長,我有間單獨的辦公室, 沒叫我遷出),倒是對我光罵、光諷刺,沒打。
最後宣佈結論,沒有查出反動的思想行為,可結束審查,恢復工作。但因為在運動中與大家的感情大傷,不利於今後的協作,故調動工作單位,由市衛生防疫站調到市衛生局工業衛生科,任副科長。
吃一塹長一智。我知道黨一直對我不放心。知道有許多“雪亮的眼睛”和豎起的耳朵在伺察著我的言動,我不得不小心謹慎。剛直不如隨風倒,多點頭,順領導,不同意見少發表。要緊的是,決不可再提“肅反對我搞錯了”,因為成績是主要。
但我的工作積極性仍絲毫不減,不斷下廠礦,為維護工人健康出力,確實滿心感到光榮。煉鋼工人引導着火紅的鋼水,大汗淋漓;煤礦工彎腰在地底“掌子面”用風鎬電鑽鑿岩、煤石粉塵撲面,還形成塵肺;紡織女工在潮濕車間裏忙碌,風濕病高發,化工廠的有害氣體撲鼻後沉積於體內……我要為他們保駕護航。
每年年終鑒定時,同事們對我的工作積極、肯鑽研,不謀私利、不搞幫派,都是一致承認的。至於生活樸素、作風正派,多數人都同我一樣。(未完待续)
有一次,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舊“太廟”)看籃球比賽,見朱德總司令穿件白襯衫與普通觀眾坐在一起,只是身邊有個警衛員。一股工農解放、男女平等、服務光榮、改造陋習的清新之風使社會生機煥發。誰要是訓斥群眾、強迫命令、拖宕工作,就是沿襲“國民黨作風”,會被同志嚴厲批評。
寄託著四川百姓四十年願望的成渝鐵路兩年多便建成通車了。大家對國家前途滿懷信心和熱情。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均慷慨解囊,我們敢同美帝較勁,多麼揚眉吐氣。街頭活報劇中美國總統氣急敗壞的小丑形象,總是笑駡的活靶子。
1951年冬,我參加中央土地改革團華東第六團到安徽阜南縣搞了兩期土改共三個多月。讓農民明白“誰養活誰”和如何劃分階級,把地主的五大財產(土地、房屋、牲畜、大農具和浮財)分給貧、雇農和下中農,也給地主按人口留一份。富農的多餘生產資料也要徵收。土改結束離村,男女老少敲鑼打鼓放鞭炮,排成長龍送我們走出幾里地,的確是由衷的熱烈。
“我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立法委員,逃往臺灣了”——這塊大石壓在我背上,是我的原罪。“清理中層”忠誠老實運動,三反運動後期向党交心、重點“解剖”……我一次次在黨內外的會上批判父親對我的思想影響,向朱德學習——背叛所出身的家庭,向無產階級徹底投降。我說:我父親叫我在亂世中“搶讀”,希望我成名成家;還督我學四書、讓我們辦《家風》報,不斷灌輸封建思想;我吃剝削飯長大,思想感情與工農兵有大差距……
1953年春,讓曾學理工農醫的大學生學有所用,我被安排到市衛生局的衛生防疫部門,貫徹“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等方針。
1954年初,我與21歲的北京李姑娘締婚,她高小畢業,任區政府文書屢受獎勵,在業餘中學也是模範學生,是個處處要強、感謝共產黨給予學習培養和工作機遇的新黨員。我倆在許多方面互學互補,她處人比我平易、謹慎,更能替別人著想。後来,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很優秀,一個是英語高級教師,另一當過外貿公司的副總經理。
第二樂章 沉重 (1955~1978)
1955.7由反胡風開始的“肅反”運動把我“揪”出來大審大批了半年,主要是父親和其他“反動親屬”與我的關係,需滴水不漏地向圍攻我的幾十位群眾從頭敍述,一一回答他們的質疑,然後寫成文字,再問、再答、再寫……外調同志根據線索四處尋詢證人,讓他們詳寫旁證材料。
有個市衛生防疫站同志,過去曾與我私下談心,在會上似乎頗有奇貨可居,大揭我談的家庭狀況、上學經歷以及對防疫站長、同事的一些看法(倒是沒怎麼添油加醋),好在我確沒有對中共和領導人不敬,也沒把柄落在他手。
在這半年中,停止了我的業務工作,讓我獨自呆在辦公室裏(作為市衛生防疫站的衛生科長,我有間單獨的辦公室, 沒叫我遷出),倒是對我光罵、光諷刺,沒打。
最後宣佈結論,沒有查出反動的思想行為,可結束審查,恢復工作。但因為在運動中與大家的感情大傷,不利於今後的協作,故調動工作單位,由市衛生防疫站調到市衛生局工業衛生科,任副科長。
吃一塹長一智。我知道黨一直對我不放心。知道有許多“雪亮的眼睛”和豎起的耳朵在伺察著我的言動,我不得不小心謹慎。剛直不如隨風倒,多點頭,順領導,不同意見少發表。要緊的是,決不可再提“肅反對我搞錯了”,因為成績是主要。
但我的工作積極性仍絲毫不減,不斷下廠礦,為維護工人健康出力,確實滿心感到光榮。煉鋼工人引導着火紅的鋼水,大汗淋漓;煤礦工彎腰在地底“掌子面”用風鎬電鑽鑿岩、煤石粉塵撲面,還形成塵肺;紡織女工在潮濕車間裏忙碌,風濕病高發,化工廠的有害氣體撲鼻後沉積於體內……我要為他們保駕護航。
每年年終鑒定時,同事們對我的工作積極、肯鑽研,不謀私利、不搞幫派,都是一致承認的。至於生活樸素、作風正派,多數人都同我一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