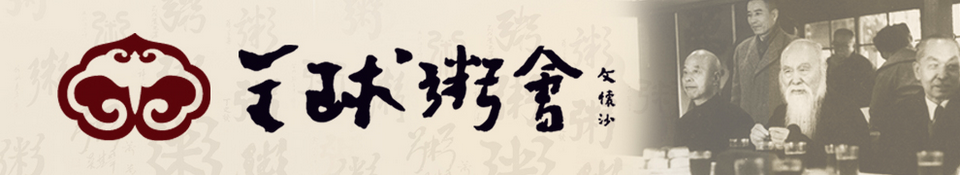不订报读报久矣,近年来相关消息,多来自网络和电视。今天华视晨间新闻,播出一则文教短讯,说是台大即将卸任的校长李嗣涔,在最后一次主持开学典礼上,提醒大一新鲜人,在这里若遇挫折,要学习当创新的唯一,而不是只当第一名,学得主动,活得从容。李校长此话深得我心,岂止台大人理当如此,所有新鲜人皆应如此;将近一甲子前,就读台师大时,三位教授也如此开导过,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对我产生极大影响。
第一位是江应龙老师,字际云,辽金元文学专家,教我们大一国文,课外读物多为自己近作,而创作文类又以论述和散文为主。我偏爱老师的散文,虽说作者自认「只是广阔的文学苑囿中的一根小草、一朵小花而已」,实则是忧患时代的见证,有现实的批判和家国之爱,更因为文字洗炼平实,尤其内容言之有物,读者不受到感动几稀。
江老师时常要我去『潜庐』,用别号取名的小书房,一面浏览藏书,一面代改考卷,偶尔还会丢出几句启示金言,有如鼓励我试着投稿,把报章杂志当作园地,写作要学得主动,活得勤快且从容,嘴边话是「孩子,好好学着点」!
当年老师很抬举我,说是成绩老拿第一,功课好并不稀罕,创作永远是唯一,才是人生永恒的追求,所以特别对我有两大要求:其一、课余得勤于习作投稿,这点我是很快勉力做到了。因此在每年元宵的『中副』(『中央日报』副刊)三者(作者、读者、编者)联谊茶会里,每次会面总是拉住我手,似以有此“得意”门生为傲,频频向人跨耀,并举荐参加了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征文,竟也不负所望,侥幸荣获大专组首奖,为老师争光。
其二、江老师三番两次要收做“义子”,关于这一点,我是忤逆了好意,始终没有答应下来,以致于后来在文化人士雅集,台北粥会的每月例会中,偶尔碰面都有些难为情,为避免彼此间尴尬,我有一阵子极少出席粥集文会,工作繁忙纯粹借口,真正原因说不出口。某年惯例“父亲”与义子女过年,某位知名作家受命再帮邀约同往,考虑再三依旧婉辞,事隔多年,及今思之,多少仍有那么一点歉疚,对不住恩师的盛情厚爱。
印象中值得记述的第二位大学教授,是教我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四书的杨宗珍老师,她原本只在台师大兼课,很早便从事于写作,最早向『中央日报』的『妇女周刊』投稿,第一篇文题:《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自此开始用“孟瑶”的笔名,活跃于台湾文坛,笔耕之外,又酷爱国剧(即京戏、平剧),并能票戏,常粉墨登场。在课堂里,杨老师就强调,要学得主动,兴趣要多方面,而且要靠培养,所以我除写作外,另致力于刊物编印,大二甚至接下『师大校友月刊』总编辑,因她久任各刊主编乙职达半世纪。
影响我大半辈子的第三位老师,是教国音学门的艾弘毅教授,所谓“国音”实即国语正音,对像老师这样大陆北方人来说,满口接近北京话的普通话轻而易举,然而南方人特别是闽台人士,每想咬字该不该捲舌?可就容易咬到舌头,因此我的大学成绩单,各科全都是A,唯独这门得B;1965年结业时,面见艾老师有所抱怨,回应一句话颇有道理,「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要刻意去想,该不该捲舌,自然说得准确,这就是从容」。从此我照着练习,从容不廹,日见成效,不仅被人称赞国语标准,尚且在本业之余,成为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前后几近30年以“卖声”为副业。
如今已老朽的我,胆敢自嘲兼自诩,当过第一更做唯一,着实都得感谢江应龙、杨宗珍、和艾弘毅教授,这三位恩师的教导有方,让我学得主动,一直活得从容。当然也顺带要谢谢李嗣涔校长,这位我认识于国防部前参事任内、具有特异功能的科学家之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