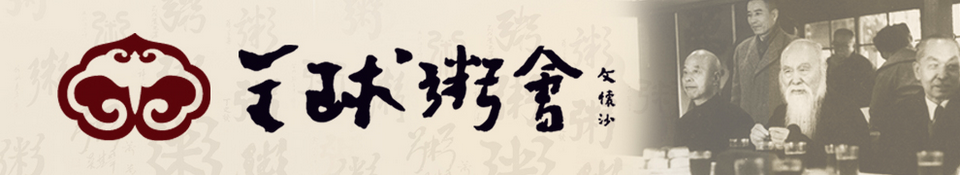我是余光中的秘书(下)* 余光中
更新时间:2014-05-26 来源: 发布:邵隆美 浏览: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仍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的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合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存都熟悉,一部《梵谷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她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平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存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回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的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信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摘自《余光中幽默文选》天下文化出版)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仍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的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合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存都熟悉,一部《梵谷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她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平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存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回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的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信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摘自《余光中幽默文选》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