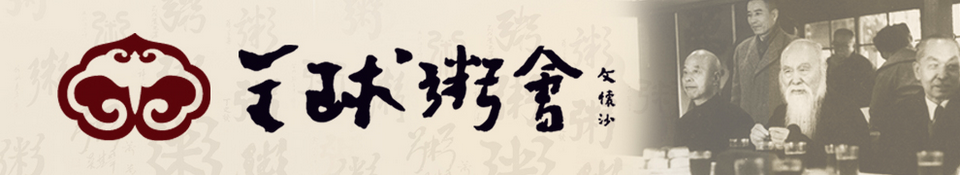宋教仁的“汉族”观(上)* 迟云飞
更新时间:2013-03-11 来源: 发布:迟云飞 浏览:
清末民初,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阶段。而其间呈现的形式,则多种多样。我们现在常用的“汉族”概念,也是当时潮流之一端。以往学界多注意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汉族”概念使用上的影响,笔者注意到,其实宋教仁使用“汉族”概念也很突出,是他的民族意识的重要部分,学界至今尚未注意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治下的人曾自称“华”、“夏”、“华夏”等,汉代以后,又有“汉人”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大体与“蛮夷戎狄”之类生活在华夏周边的落后民族相对。这些称谓,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某种意义上,她像一个文化概念,只要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就是华夏,反之,就是夷狄。有时候,她又像血缘或血统的概念,即与种族概念类似,但是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或后来的汉族,其血缘并不固定,不说远古时代所谓华夏就是各个民族融和起来的,就是汉代以后,也有东晋南北朝等多次的民族融合。所以,我们今天理解的“汉族”,有血缘的因素,但更多是文化的。
实际上,民族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如果一群人自己认为是一个民族,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当然,从客观的角度观察,民族必须拥有自己的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记忆,才会成其为民族,或者才会自己认同为民族,否则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同化。
毋庸否认,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一词,是在列强东来,中国遭受欺辱侵略的情况下,在新知识人中间产生的,其出现和使用,相当程度源于对满清贵族统治的不满。
在反复研读宋教仁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宋教仁也是一位较多使用“汉族”概念的革命家。那么宋教仁所理解的是怎样一个汉族呢?
1904年11月10日,宋教仁由湖南向湖北逃亡途中,曾写长歌,其中有“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虏骑遍于道路兮……嗟神州之久沦……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就现存文献来说,这是宋教仁第一次用“汉族”这一概念。这虽只是一首诗,信息不多,按我们仍能从中感受一些问题。在诗里,“汉人”和“汉族”意思基本相同,明确与“虏”区别和相对,强调的是与“虏”也即满洲人不同的一群人。“汉族”和汉族的栖息地已被征服,汉族人久已失去自由,宋教仁要做的,就是努力争回汉族的自由(“欲完我神圣之主义”)。
1905年,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发表《汉族侵略史•叙例》,在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中,宋教仁用了34个“汉族”。文章的开头便说:「集合四百五十余兆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方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历史学上之关系,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其地理学上之分布,除本族范围之外,且蔓延于马来、澳洲诸岛屿,更越太平洋而遍及于亚美利加之大陆,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
这段话,并不是为汉族所作的严格的定义,但包含了宋教仁对“汉族”的理解,或者说,是在这些条件基础上的认同。我们试分析这段话显示的“汉族”的涵义。首先是血缘和血统,具有这个血统的人民有四百五十余兆(四亿五千万),这些人民的共同祖先是黄帝,本文后面所述的所谓“汉族侵略史”,就是以黄帝的征服活动为开端。这个角度多少接近我们现在说的种族。汉族是“神明聪强”的,是优秀的民族,这不是民族沙文主义,也没有歧视或贬低其它民族的意思,而是为了在中国备受列强欺辱情形下给自己也是给同胞增强信心,其它的赞美语言亦当如是理解。如邹容所说:“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都是一个意思。其次是文化,宋教仁提到几个要素,共同的语言——汉语,已应用了“五千余年”;共同的文字——汉字,“完富美备”,有 “一万四千余形”;共同的历史,我们后面再介绍。另外,生活的地域,宋教仁说,除了本土的“四百六十余万方哩”之外,还蔓延于世界各地。
有时候,“汉族”又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如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说:“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当然,此中国的涵义中,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里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宋教仁包括许多革命党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实际上与对汉族自身身份的认同几乎是同步的,并且是混杂在一起的。那么,“汉族”历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在宋教仁看来,是黄帝之时。这在清末新知识人中几乎是个约定俗成的做法。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刊印黄帝肖像,文中在序之后的第一段,题目就是《黄帝肖像后题》。陈天华把黄帝称作“始祖公公”,他那充满激情的笔写道:“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想当初大刀阔斧,奠定中原,好不威风。到如今,飘残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风吹萍叶,莫定西东。”然后,陈天华也用了“汉族”这一概念。(未完待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治下的人曾自称“华”、“夏”、“华夏”等,汉代以后,又有“汉人”之类的称谓。这些称谓,大体与“蛮夷戎狄”之类生活在华夏周边的落后民族相对。这些称谓,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某种意义上,她像一个文化概念,只要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就是华夏,反之,就是夷狄。有时候,她又像血缘或血统的概念,即与种族概念类似,但是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或后来的汉族,其血缘并不固定,不说远古时代所谓华夏就是各个民族融和起来的,就是汉代以后,也有东晋南北朝等多次的民族融合。所以,我们今天理解的“汉族”,有血缘的因素,但更多是文化的。
实际上,民族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如果一群人自己认为是一个民族,那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当然,从客观的角度观察,民族必须拥有自己的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记忆,才会成其为民族,或者才会自己认同为民族,否则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同化。
毋庸否认,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一词,是在列强东来,中国遭受欺辱侵略的情况下,在新知识人中间产生的,其出现和使用,相当程度源于对满清贵族统治的不满。
在反复研读宋教仁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宋教仁也是一位较多使用“汉族”概念的革命家。那么宋教仁所理解的是怎样一个汉族呢?
1904年11月10日,宋教仁由湖南向湖北逃亡途中,曾写长歌,其中有“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虏骑遍于道路兮……嗟神州之久沦……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就现存文献来说,这是宋教仁第一次用“汉族”这一概念。这虽只是一首诗,信息不多,按我们仍能从中感受一些问题。在诗里,“汉人”和“汉族”意思基本相同,明确与“虏”区别和相对,强调的是与“虏”也即满洲人不同的一群人。“汉族”和汉族的栖息地已被征服,汉族人久已失去自由,宋教仁要做的,就是努力争回汉族的自由(“欲完我神圣之主义”)。
1905年,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发表《汉族侵略史•叙例》,在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中,宋教仁用了34个“汉族”。文章的开头便说:「集合四百五十余兆神明聪强之血族,盘踞四百六十余万方哩肥美膏腴之地壳,操用五千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一万四千余形完富美备之文字,其历史学上之关系,实为东洋文化之主人翁,其地理学上之分布,除本族范围之外,且蔓延于马来、澳洲诸岛屿,更越太平洋而遍及于亚美利加之大陆,其人类学上之价值,则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即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
这段话,并不是为汉族所作的严格的定义,但包含了宋教仁对“汉族”的理解,或者说,是在这些条件基础上的认同。我们试分析这段话显示的“汉族”的涵义。首先是血缘和血统,具有这个血统的人民有四百五十余兆(四亿五千万),这些人民的共同祖先是黄帝,本文后面所述的所谓“汉族侵略史”,就是以黄帝的征服活动为开端。这个角度多少接近我们现在说的种族。汉族是“神明聪强”的,是优秀的民族,这不是民族沙文主义,也没有歧视或贬低其它民族的意思,而是为了在中国备受列强欺辱情形下给自己也是给同胞增强信心,其它的赞美语言亦当如是理解。如邹容所说:“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国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都是一个意思。其次是文化,宋教仁提到几个要素,共同的语言——汉语,已应用了“五千余年”;共同的文字——汉字,“完富美备”,有 “一万四千余形”;共同的历史,我们后面再介绍。另外,生活的地域,宋教仁说,除了本土的“四百六十余万方哩”之外,还蔓延于世界各地。
有时候,“汉族”又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如宋教仁的《烈士陈星台小传》说:“使天而不亡我汉族也,则烈士之死贤其生也;使天而即亡我汉族也,则我四万万人其去烈士之死之年几何哉?”当然,此中国的涵义中,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这里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宋教仁包括许多革命党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实际上与对汉族自身身份的认同几乎是同步的,并且是混杂在一起的。那么,“汉族”历史的开端是什么时候呢?在宋教仁看来,是黄帝之时。这在清末新知识人中几乎是个约定俗成的做法。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刊印黄帝肖像,文中在序之后的第一段,题目就是《黄帝肖像后题》。陈天华把黄帝称作“始祖公公”,他那充满激情的笔写道:“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想当初大刀阔斧,奠定中原,好不威风。到如今,飘残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风吹萍叶,莫定西东。”然后,陈天华也用了“汉族”这一概念。(未完待续,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由宋教仁常德研究会提供)